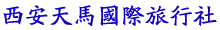弄堂里的嬉戏、市井中的吆喝、梧桐下的剪影……上海的老街小巷,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、道不完的情义,让人回味无穷。
今天本版邀请的这位忆往者,回忆了很多上海老弄堂里的故事,正像他说的,“上海滩的马路、街坊何其多,但只有透出人文气息的才是令人回味的,只有说得出故事的才是让人魂萦梦绕的,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人才会斤斤计较于它的些许变化,哪里变糟了,哪里变味了,哪里变得更可人了,甚至哪里消失了……”
“上只角”居民的独门荣耀
每当路过西藏路、福州路口的来福士广场,心中总泛起一种无可名状的情绪,因为在这栋钢筋水泥建筑所在的土地上,有着我童年记忆中的乡愁。
此前,这里是旧式里弄中著名的会乐里。据史料载,1904年,浙江南浔富商刘景德买下了这个地块,建成老式里弄,取名会乐里。到1924年又扩建,主弄左右对称,各有4条横弄,弄门为简式牌坊,上写“东一弄”、“西一弄”等,共28幢楼房,均为新式石库门。弄口设在福州路,号牌为福州路726弄。会乐里的出名,并非是因其地段位置,而是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,这里是旧上海的妓院,俗称“长三堂子”。解放后,妓院被封闭,会乐里改邪归正,大批市民搬迁至此。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,旧区改造的铲车又把会乐里从物质形态上消灭了,从此,会乐里彻底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我小时候就住在会乐里。它的地理位置是优越的,人民广场近在咫尺。那时的人民广场里有一根根石柱擎起类似宫灯一样的照明灯,大概有72盏吧。石柱基座是石砌的大圆盘,敦实且漂亮。圆盘的缘口有两层,底下那层可供人歇脚,坐着晒太阳或乘凉,小孩子则在上面爬上爬下闹着玩。我们会乐里的人称人民广场为人民大道。小伙伴吆喝着到大道里白相,踢球、练自行车,甚至约架都在大道。打群架进了派出所,就说进“老派”了,从派出所放出来,就说出“老派”了,进出“老派”次数多的,自然就成了孩子王,人称“一只鼎”。
最令人期盼的当然是每年十月一号晚上放焰火,焰火在人民广场比邻的人民公园发射。那是会乐里居民骄傲的时刻,因为坐在会乐里石库门前看焰火,犹如一排一座。每到那时,亲戚朋友会在道路交通管制前,早早赶来蹭左邻右舍的竹榻、藤椅、长凳、小方凳、小矮凳,享受“上只角”居民的独门荣耀。
到了第二天,我们小伙伴三五成群,赶在清洁工扫街之前到大道里捡拾“烟火头子”,就是焰火燃烧未尽的火药子。那是一些长约一二公分,直径半公分左右的圆柱形银白色的物体。为了觅得这些小东西,小伙伴们满广场找寻,眼神好的捡得一小包回家,在弄堂里将几个小东西用废纸包起来,擦火柴点着纸,引燃小东西后,这些火药会喷射出各种绚丽的火花。有一次火点燃后,我爬到旁边人家的窗台上看,不料一束火花直奔我脸上而来,我本能地用手挡脸,手背上有一处顷刻被灼伤成白色,痛得我即刻跳下窗台,冲到后门灶披间水斗旁,拧开水龙头冲洗。事后留下的点点疤痕,隔了很多年才褪去。
碗对碗的实质是情对情
会乐里主弄和横弄四通八达,这里是孩童乐园。那时我们在弄堂里玩过摔跤,青春荷尔蒙在肉搏中尽情挥霍,在实践中学会了摔跤的技巧性动作,如“大背包”、“小背包”、“扫堂腿”、“锁手”、“绊腿”、“大搭”、“小搭”、“三角头颈”、“反关节擒拿”等不一而足,且无师自通。还有好玩的就是“斗鸡”,把一条小腿抬起来,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之上,用手扶着形成三角形状,另一条腿金鸡独立,跳跃着用抬起那条腿的膝盖作为战斗武器,或撞、或顶、或撬、或压,进行角力,这里比的是力量,是技巧,是耐力,是斗志。“斗鸡”既可一对一斗,也可一对多斗,也可多对多斗,大冬天一场斗下来,汗流浃背。
弄堂里也有高雅的体育活动,如打“台球”,就是打乒乓,而所谓的台,只是水泥的洗衣台,拿两块砖,中间架上一根细竹竿就能开打了。至于乒乓板,常常是不贴海绵胶皮的光板,乒乒乓乓不一会儿就把球打裂了。还有就是打板羽球,三根鸡毛插在一个圆形橡皮包着的软木中,称之为三毛球,比赛为六分制,赢者续打,摆大王,输者下场,轮流上阵。
有一天,我发挥得好,连续摆大王几个小时,乐极生悲,晚上发烧到39.8℃,高烧几天不退,住进了仁济医院,诊断下来是急性淋巴结炎。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,烧退后下床进厕所小便,小腿肚直发抖。老话说祸兮福所倚,在“养病”期间我才知道食品中还有麦乳精、蜂皇浆。麦乳精不仅可冲水喝,还可趁大人不注意直接舀一勺放在嘴里抿着吃,闷声不响地独享满口的香甜。
会乐里东三弄靠近云南路出口过街楼下有个公用电话间,看电话的老阿姨、老爷叔对每家每户的人头情况都了解一二。碰到来电话,靠得近的就不挂电话径直叫来听话人,这样就为接听电话的人省下了三分钱。但距离较远的只能挂电话,传呼到人打回电。谁家儿子女儿到了20岁左右有了恋爱对象,老阿姨、老爷叔也会喊漏嘴,“某某某,女朋友叫侬打回电。”弄得几个号牌的石库门都知道谁在谈朋友了。
当时弄堂里洗衣晾衣都是穿在竹竿上,用丫杈头丫到客堂、天井的顶上,竹竿两头搁在天井、客堂建筑构件上,有的直接把竹竿撑到弄堂里。遇到下雨,只要主人不在,隔壁人家也会将衣服代为收起,叠放整齐,等到主人回来送上门。即使不是过节,只要哪个邻居家下馄饨、饺子了,一般情况下,隔壁人家总会共享一碗,而受惠的一家不会空碗回过去,总要在碗里放些食物回礼,哪怕是几块糖果,碗对碗的实质是情对情。这种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、相濡以沫的朴素气氛恰恰是现代化居住社区里所稀罕的。
在会乐里拆除前,我曾拿着一部小型摄像机进入到已衰落破败的会乐里。孩提时代眼中的大弄堂感觉小了,横弄堂显得窄了,业已搬迁过半的弄堂,已没有了往日的活气。老邻居的目光看着我,似曾相识的迟疑、揣测让我莫名惶恐,全然是时光容易把人抛的心境。
人行道上的西瓜摊
在物资短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饭店、大商场与我们是无缘的,真正接近我们的是一些小店家。比如丰实水果店市口极好,在西藏路福州路口的东西角上。店里的水果有香蕉、黄蕉、红玉、国光苹果、莱阳砀山梨等。到了过节,装点家中果盘的多数还是0.28元一斤的国光苹果。生梨中最便宜的是水分少、肉质粗的木梨。买什么是由家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,到夏天跨门营业,卖西瓜出摊至人行道上。竹编的箩筐里长的是平湖西瓜,圆的是8424,长长桌上放着一把长长的西瓜刀。平湖瓜被切开后露出黄瓤黑籽,8424切开后红瓤黑籽,坦露出来,煞是好看。这些瓜被切裁成一片一片,每片或五分钱或七分钱,吃来爽口解暑,与八分钱一根的雪糕相比,西瓜块的性价比来得高。片片瓜瓤使夏夜的熏风里飘荡着一缕缕鲜果的清香气息,卖瓜的则一声高一声低的吆喝叫卖“西瓜煞拉里甜额来”、“保开西瓜只只熟额来”,吴侬软语飘进周围乘凉摇扇人的耳里。这时大人会从兜里掏出零碎铜钿,给身边孩子买片西瓜解馋。
如果遇到西瓜大量上市,四分钱一斤的时候,家家户户会买上几只放在家里,吃的时候用井水浸半天,晚饭后用菜刀剖开,听到“扑”的一声,就知道买到熟瓜了。吃罢西瓜,把瓜皮留着,切掉绿皮,就是中医称之为西瓜翠衣的物事了,撒搓上盐花,稍后揉捏再晾干,可以生拌着吃,也可以作食材炒着吃。西瓜籽洗净晒干,用铁锅炒西瓜子吃也是不少人家的家务活。
丰实水果店旁边的文具店,现在已变身为餐饮茶室了。想当初这爿文具店却是颇有气势和派头的,虽是小小文具店却有两个楼面,身居西藏路、汕头路口,门面直对宽阔的人民大道。当时每到新学期来临,新课本下发后,我们会在文具店里买包书纸将新书包起来。黄褐色的包书纸因为纸质柔韧,被誉之为牛皮纸。店里面的木质铅笔有铅笔一厂、铅笔二厂生产的硬铅、软铅、粗铅、细铅。记得橡皮是2分钱一块,画图用的大号橡皮是5分钱一块,与之相匹配的当然是方方正正的画图用的“开化纸”了。等到可以调换铅芯的活动铅笔出来后,小伙伴们又在下课后走进文具店买铅笔芯,铅笔芯在笔管里调进调出,弄得两只小手黑乎乎亮光光的,也成就了一番童年记忆。
丁香饭店的阳春面与肉皮汤
与丰实水果店形成掎角之势的西北角上的丁香饭店,解放前是万寿山酒楼。我无缘看到当年酒楼的阳春白雪,但却领略了丁香饭店的下里巴人。
上海人偶然也消费得起的,就是9分钱一碗的阳春面,葱花碧绿生青,面条软硬适中,宽汤细面,又香又鲜,既能果腹,又有口舌之娱。现在宾馆里也有所谓的阳春面供应,尽管有其色,但未必有其味,始终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,吃到最后,回味下来,顿有所悟,是油腥不对,若无猪油,哪有沪上阳春面香呢?
阳春面其实就是清汤光面,其素面朝天的阳光模样,使上海人想到了“阳春”这个高雅脱俗的好名字。当年的这款大众点心,现在成了外省市人口中的上海招牌点心。此味只应昔时有,如今已无少时味。
光面主要解决温饱,如要增加营养,在面上加肉丝,或鳝丝,或爆鱼,或辣酱,或素鸡,或大排、小排,光面上加的这些食料,称之为“浇头”,就是因人而异个性化了,所谓丰简自便,各由其人。现在政府出台的一些民生政策,也有普惠制上加因人而异的“小灶”,上海人就形象地称之为“阳春面加浇头”。
丁香饭店称为饭店,当然供应饭菜。进入我孩提时代的食谱记忆中的是8分钱一碗的肉皮汤。肉皮汤的肉皮是猪腿肉上“批”下来的,砧墩师傅用薄刀将皮上肉剔净,皮张剔得越薄越好,将肉皮晾在风中阴干,让油在通风环境中耗完,再放到大油锅中炸松,然后放入水中浸发,等到肉皮浸泡得松扑扑如海绵状后再切成小块入高汤煨透。此时肉皮内浸润透了高汤的鲜美,肉皮松软,入口滑腻,唇抿齿嚼,鲜味从松软的肉皮中渗出,游移在唇齿之间,让人回味无穷。小时候弄一碗肉皮汤回家也算开荤了,所以那时候买一大碗肉皮汤却要带一只小钢宗镬子去,为的是让饭店多加一勺汤,拿回家可供全家享用了。记得寒冬腊月天,用滚烫的肉皮汤淘饭,再加入点自家制作的烂糊肉丝,吃下去浑身暖意浓浓,成就了一番肃杀萧条的冬天里温馨的回忆。
羊肉薄如蝉翼欣赏刀功饱眼福
丁香饭店朝东贴隔壁有一小弄堂是会乐里的小支弄,这个小弄堂口开有一爿熟食店,每到中午、晚上两个市口总有七八个人排队买熟食,隔着玻璃橱窗,看看浓油赤酱的肉食和鱼肴,鼻息里混着豆制品的五香味,饥肠辘辘中勾起食欲无限。
那时包装食品还没塑料袋,基本上是土黄色的牛皮纸当道,倒是很环保原生态的。店内的师傅用秤称好熟食后,把熟食在木砧上一放,用菜刀斩好码齐,摊放在牛皮纸上,量小的用手包成三角包,量稍多的包成四方包,如果谁一次买了三四包就是家里请客开大荤了。
手里捧着三四个牛皮纸包走进弄堂里,一定会吸引住不少小孩子的目光和鼻息,这目光会一直把你送得很远。当然,较受寻常人家青睐的当数猪头肉了。牌子上写着“白切猪头肉”,7分钱一两,这种极具草根性的肉食一般买上三两左右,就可以回家渳老酒了。
熟食店的隔壁是米店,洋粞米、粳米、标准粉、精白粉、切面、馄饨皮子等等一应俱全。米店朝东就是会乐里总弄堂口了,而紧挨弄口有个小烟杂店,勇士牌、飞马牌、牡丹牌等香烟可以成包买,也有论支买的,生意做得很活。再旁边就是惠民药房,一开间门面,但大众化药品却是齐备的。
紧邻药房的是大西洋西菜社,后来又改名为清真饭店。店里最有名的是涮羊肉,小时候听大人说,涮羊肉很贵也很鲜美,但我想不通,切得薄如纸片的羊肉怎么有肉味呢?半生不熟的半透明的羊肉怎么会比红烧肉好吃呢?但下课回家路上,我和小伙伴们会在饭店外,隔着透明玻璃窗向里望,看砧板师傅把冻成块的羊肉,用薄刀切出极薄极薄的如蝉翼般的羊肉片,欣赏刀功饱眼福。
西藏路的西侧道上以前还有一排明亮且卫生的男女公共厕所,当时无论从规模还是整洁上衡量都堪称上品。这排厕所面东背西,而背西紧贴的就是人民公园,如厕者从窗口望出去都是葱郁之色,五官感受到的是鸟语花香。清晨如厕者的基本主体是周围的居民。群众的嗅觉最灵敏,对这地利带来的福利,人民群众是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,不会错过的。所以每天清晨总能看到不少人行色匆匆地从弄堂里窜出,跨过西藏路,直奔厕所而去。
还值得称道的是厕所的外面有一排阅报栏,从 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,一直到 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一应俱全,如厕减轻了生理负担,再神清气爽地博览群报,汲取精神营养,生理上除垢和精神上吸收养料在此得到完美结合。
书香扑面的福州路
福州路是现今上海著名的文化街,其文化底蕴却是有历史渊源的。在福州路的街面上,尤其是湖北路至河南路之间,卖文房四宝的商店鳞次栉比,店多成市,产生了集聚效应,再加上新华书店、古籍书店、外文书店等,真给人书香扑面之感。
在儿时记忆中印象较深刻的是朵云轩、周虎臣笔庄、百新文化用品商店等。且说河南路口的新华书店,“文革”刚结束时,该书店两楼不公开对外营业,但知情者也可随意进入购书的所谓内部参考书出售处,书架上有诸如 《病夫治国》《卡扎菲与利比亚》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等书籍。那时只要有空我就钻到二楼,在书架上找书买书,心中还常有享受“特供”的一份窃喜。在上世纪70年代,福州路上的笔墨纸砚不少都是自制自销的,为的是维护品牌的声誉,有的甚至是前店后厂,所以顾客基本上无购入伪劣商品之虞。
福州路过了云南路往东还有青莲阁茶楼、陆稿荐肉庄、四马路菜场、浙江电影院等,都是和平民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去处。茶楼在上世纪60年代已逐渐转变为饭店,陆稿荐肉庄在60年代还是卖肉的正宗场所。四马路菜场则是市中心最大的室内菜场之一,和虹口区的三角地菜场、卢湾区的八仙桥菜场等齐名。每天早上五点多,这个上下两层的菜场就人声鼎沸起来,各色蔬菜、肉类、水产品、豆制品、家禽、腌制品、配料齐全的盆菜,甚至还有熟食柜台。现在这个颇负盛名的室内菜市场已不复存在。尽管如此,老菜场的“阴魂”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。我曾特意在福州路、浙江路寻访,看到原菜场的外面路边尽是卖蔬菜的小贩,吆喝声不绝于耳。
在原菜场的对面,浙江电影院依然健在。这家影院当时是闹市区票价最便宜的,因为影院里不是沙发椅子,而是连排的木头椅子,散场时,座板弹起来,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,但学生们还是经常光顾这家便宜的影院。学生票有时只有一角,甚至有过8分钱一张的。我在这家影院里就看过 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地雷战》《羊城暗哨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等黑白电影。
上海滩的马路、街坊何其多,但只有透出人文气息的才是令人回味的,只有说得出故事的才是让人魂萦梦绕的,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人才会斤斤计较于它的些许变化,哪里变糟了,哪里变味了,哪里变得更可人了,甚至哪里消失了……
老街弄堂
上海滩的马路、街坊何其多,但只有透出人文气息的才是令人回味的,只有说得出故事的才是让人魂萦梦绕的,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人才会斤斤计较于它的些许变化,哪里变糟了,哪里变味了,哪里变得更可人了,甚至哪里消失了……